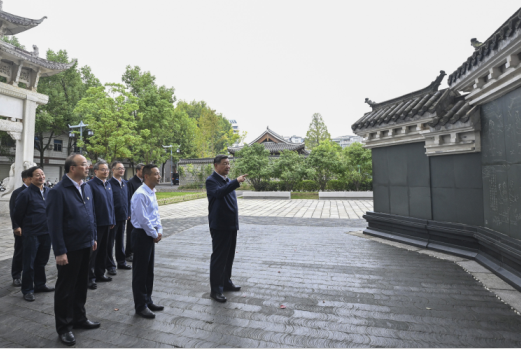南方人爱吃米饭,北方人爱吃面食。
米饭的做法简单,无非蒸和炒,且品种单调。而面食花样就很多了,就烹饪方式言,有蒸、炒、煮、烙等;就呈现方式言,有干面和汤面;就品类而言,五花八门,名目繁多,若以地域分的话,著名的就有陕西油泼面、兰州拉面、新疆拉条子拌面、山西刀削面、河南烩面片、河北炸酱面等等;若以形状、做法、口味去分的话,那就更多了。
北方人爱吃面,但要说最爱吃面的,非陕西人莫属了。就连面食的品类,陕西也是北方乃至全国花样最多的了。陕西的面食文化,历史也很悠久,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。在首届中国面食文化节上,84岁的中国饮食专家王明德说:“世界面条故乡在中国,中国面条故乡在陕西。”
在陕西,除了几种全省通吃的面食之外,各地也都有各自特色面:岐山臊子面、户县摆汤面、蓝田旗花面、大荔炉齿面、韩城大刀面、永寿长寿面、汉中梆梆面、安康窝窝面、定边荞剁面、耀州咸汤面、麟游血条面、富县鸡血面、礼泉羊肉合面、乾州酸汤挂面、潼关一窝丝扯面、三原疙瘩面、陕北的杂面等等。由于花样繁多,且一直不断推陈出新,有好多我还不曾吃过,这里也就不具体罗列和详细介绍了。
陕西人爱吃面,但并不见得全国各地所有面陕西人都爱吃。陕西人偏爱的是陕西人自己做的陕西面。陕西人吃面,对原料、做法、调料都特别讲究,所以也就很挑剔。兰州拉面、新疆拉条子,因为这两个地方和陕西同属于大西北,口味上比较接近,陕西人还能吃;河北的炸酱面、河南的烩面片、山东的清汤面等,多数陕西人吃不惯,因为他们那里的面粉没有陕西的品质好,做法也没有陕西人细致,调料配比也不适合陕西人口味。
我是一个正宗的陕西人,以前在老家的时候经常吃面,在西安这十几年也是以面食为主。这些年,由于工作的关系,我经常去外省出差,也吃过不少其他地方的面:在成都,我吃过铺盖面、勾魂面、担担面,虽然口味有些偏麻,但挺喜欢;在郑州,听说当地的烩面片全国闻名,我曾打的在全市找最好的烩面馆,但是吃过之后觉得很遗憾,打死再也不吃了;在山东的章丘、寿光,我吃过清汤面,碗很小,面很嫩,菜很少,汤里只有很重的盐味,看着不香,吃着难受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寿光,有一天晚上,我打车到处找面吃,好不容易找着一家面馆,我问老板会不会做油泼面,老板说会啊,我用怀疑的目光看了他半天。老板看我不相信他,就说,我知道你们“陕西人是中国面食的鼻祖”,我曾经在西安呆过几年,跟一个大师傅学过面工,做油泼面绝对没问题。我说那好,你就给我做一大碗油泼面。结果等了半天,老板端上来的竟然还是一碗他们当地的清汤面。我一下子就躁气了,问他到底会不会做油泼面。他义正词严地说,这就是陕西的油泼面啊!我本想和他理论一番,教他到底如何做油泼面,但老板气咻咻地扭头走了。我无话可说,也无可奈何,坐下来硬着头皮吃了几口,实在难以下咽,就把钱放在桌子上,快步走出了面馆……
虽然其他地方的面食在陕西都有,但做法上都有些改良,以尽量适应陕西人的口味。西安是陕西省会,这里基本上包括了全国各地的面食品类,更是荟萃了陕西各县的特色面食——当然,要吃陕西各县正宗的特色面食还是要去它的发源地。比如,岐山臊子面和擀面皮,在西安也卖得很火,有个“永丰岐山面”在陕西开了数十家连锁店,已形成一个餐饮品牌。但正宗的西府人都知道,西安的岐山臊子面的做法和口味实际上已经变了样,远没有岐山当地的臊子面好吃。因此说,再好的饮食,离开了本土之后,都会失了原汁原味。这也是陕西面食在全国不能普及推广的根本原因。
陕西人不但自己爱吃面,而且常在外地人跟前夸耀陕西的面食文化。外地人来陕西作客,陕西人带他们吃的最多的当然是面食,而且会在饭桌上大讲而特讲陕西的面食文化。陕西有个著名的“八大怪”,其中一怪就是“面条像裤带”。之所以说“面条像裤带”,是说明其形状的厚、宽、长,事实也就是这样的,一点都没有夸张。其实,这说的也只是陕西面食的二三个品种,像杨凌蘸水面、扯面。陕西的面有条状的,也有非条状的,无论条状或非条状,也是有细有粗,有长有短,有厚有薄,有宽有窄;而非条状的,也是有方有圆有三角形有不规则形等等,绝不雷同。比如,岐山臊子面很细,像牙签一样;棍棍面是圆楞的,像竹筷一样;蒜蘸面是不规则的圆片儿……
只有陕西人才真正爱吃面、会吃面,对面的理解最深,对面的感情最深。陕西人能够切实感受面的魅力,且善于从面食的食用过程中得到美的享受。不少陕西人外出,若是三天吃不上面,就觉得不舒服,浑身没力气,心情很糟糕;若是外出十天半月乃至更长时间,回到家里的第一餐必定是面,而且会连吃几碗,不解馋、不尽兴,绝不肯罢休。因此,陕西人出不了远门,想“老婆娃娃热炕头”是一方面原因,更主要的是因为舍不下那一碗面啊!陕西人当然也吃米饭,但是那也只是偶尔,且每次吃完米饭,必然还要再吃上一些馍或饼来补充一下,不然会感觉肚子空、心里慌。陕西人觉得,只有吃面肠胃才舒服,只有吃面心里才实在,只有吃面才觉得生活有滋味。这是陕西人的秉性和习性,几千年来都是这样,谁也无法改变,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想着去改变。难怪外地人常说陕西人固执、倔强,是“一根筋”。
也是因为爱吃面,不爱出远门,所以有些外地人说陕西人没出息。这个就大错而特错了!爱吃面的陕西人里,从古至今,各个行业、领域都有杰出人物。古代的距离我们太远,也就不说了,光当代就有很多:习近平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,张艺谋是国际著名导演,贾平凹是全国著名作家,刘文西是全国著名画家、赵季平是全国著名作曲家,郑钧是中国当代摇滚乐坛中坚力量……以上列举的几位代表,哪一个不是“腕儿”呢?至于其他的重量级人物就更是多如牛毛。爱吃面的陕西名人,真可谓数不胜数。当然,这些年,随着社会的进步,陕西人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改变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陕西人走出了陕西,遍布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,他们常年在外奔波,经过一番拼搏,好多最终都干成了大事,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谁还敢再说我们陕西人没出息?
陕西人爱吃面,陕西面也好吃。如果外地的朋友想吃、爱吃陕西面,请你到西安来,我若有空的话,陪你专门吃面,每天一顿面,一个月不重样,保你百吃不厌,越吃越想吃,越吃越爱吃!
西府醋香
文/刘省平
人活着就要吃饭,吃饭离不开调味品。世间有五味: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。其中“酸”居首位,由此可见人们对酸味的看重。酸味的来源挺多,比如蔬菜、水果等等,但饭食调味品之酸则来自于食用醋。醋,又称为食醋、醯、苦酒等,是以麦、米、高粱或酒、酒糟等酿成的含乙酸的液体。它是烹饪中常用的一种调味品,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。
古代人类在世界各地从很早起就开始食用醋了。在中国,百人百性,当然各人的口味偏重也就有所不同。有爱吃醋的,也有不爱吃醋的。爱吃醋的人,顿顿饭离不了醋,在饭菜中放得醋多,以至于让醋盖住了其他味道;再不爱吃醋的人,多少也都会在饭菜里点几滴。这是几千年来国人的饮食习惯。
爱吃醋的人是比较多的。但具体有多少,以前好像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普查,醋厂的人或许做过,但那肯定也只是局部区域范围的调查。有好多地方的人是普遍爱吃醋的,但山西人以爱吃醋而全国闻名,民间有“缴枪不缴醋”的笑谈。
醋作为一种烹饪调味品,生活必需品,在全国各地均有酿造。由于原料、工艺,饮食习惯的不同,各地醋的口味相差很大。在北方,最著名的醋种当属明朝时发明的山西老陈醋;在南方,影响最大的有镇江香醋等。此外,较为有名的醋还有四川保宁醋、锦竹双头,浙江米醋等。
一般而言,东方国家以谷酿醋,西方国家则以水果和葡萄酒酿醋。在中国,通常认为醋在西周时开始被酿造。在西方,古埃及时期就已出现了醋。由于都是通过发酵酿造而成,在一定程度上,人们认为酒醋同源,凡是能酿酒的古文明,一般都具有酿醋的能力。
这个在“醋”字身上就能找到答案。“醋”字是一个会意字,从酉,从昔;“昔”意为“往日的”、“陈旧的”;“酉”为“酒”的简省;“酉”与“昔”组合起来表示“往日的酒”、“陈旧的酒”。
中国是酒的故乡,酒文化源远流长。因为酒醋同源,所以中国的醋文化也是相当厚重的,只是不为一般大众所知而已。相传,醋是由古代酿酒大师杜康之子黒塔发明的,因黒塔学会酿酒技术后,觉得酒糟扔掉可惜,由此不经意就酿成了“醋”。杜康发明了酒,被国人尊称为“酒圣”,那么按此推理的话,黑塔也应该被尊称为“醋圣”。但是好像从未听人这么叫过。
“酒圣”杜康和其子黑塔是陕西白水人。故而,身为醋的发源地上的陕西人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爱吃醋的一个群体了。但陕西人的爱吃醋,在国内并不闻名,让山西人给抢了风头,这就让人有些匪夷所思了。
陕西人真的是爱吃醋的,但陕西人中最爱吃醋的要属关中西府人了。你去看看,西府人最爱吃的臊子面、擀面皮、豆腐脑儿,哪一样不是醋出头呢?按西府人说法,“吃饭没醋,吃着不香。”我是一个正宗的西府人,从小就受了我们当地饮食习惯的影响,偏爱吃醋,但我吃醋可能比我们当地好多人还要凶一些。来省城西安生活十几年了,从来也没见过谁的醋量大过我。平时吃炒菜、米饭的时候,因为菜不是自己炒的,所以不能太挑剔。但吃面食的时候,我会尽量自己来调味,醋自然是要多浇一些了。每次与朋友下馆子,当服务员把已经调好的大碗面摆在我面前的时候,我首先会提起醋壶在面上浇一阵子,然后迫不及待地操起筷子“呼噜——呼噜”一口气就将老碗吃个底朝天。
朋友常为我的醋量咂舌,笑话我太爱吃醋呢。我说,醋是粮食精,吃了可以消食、开胃、美容,还能解毒、减肥;但主要的是从小就爱它,没办法啊。朋友就笑了,说怪不得你的脸上不长痘痘,身材那么“魔鬼”。我常会一笑了之。
虽然爱吃醋,但并非什么醋我都爱吃。前几年经常去全国各地出差,吃过好多地方的醋,什么山西老陈醋、镇江香醋、浙江米醋,但是我最爱吃的要算我们西府的醋了。西府的醋虽然在全国没多大名气,也没有几个响亮的品牌,但我始终认为关中西府的醋是全国最好的醋。西府的醋,多为农家以纯粮食手工酿造,供自家食用或赠亲戚邻居,一般很少有人大批量酿造对外销售。前些年,农村家庭人口多,买醋吃太费钱,所以都是自家酿造,一次酿造一年的量,然后用瓷缸封存起来,供平时一日三餐的调味。
酒的酿造过程我从未见过,但酿醋过程我可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,工艺说起来也挺复杂。以前,我家的醋都是由母亲一个人亲自酿造的。小时候,母亲通常是在暑期做醋。她先是把小麦、玉米用清水淘洗干净,在芦席上晒干了之后,倒入一个直径约为两米的竹笸篮里,加上酵曲和切碎的桃叶,拌上水,一遍又一遍地搅拌和匀;之后,把它们全部捞出来,找一个干净的地方靠墙堆放起来,蒙上塑料纸,给塑料纸外面撒上厚厚几层糠秕,最后再弄一些臭蒿蒿盖在上面。如此窝上大概一个月左右时间,母亲就把窝藏好的原料用面盆打成圆饼子,放在窗台上晒干,或者放在取掉席子和被褥的热炕上焙干。然后,再把干料饼打成碎末儿,装进一个个黑瓦缸里。这些黑瓦缸被搁在一排排高凳子上,给里面加上适量的水。经过大概二三周之后,我晚上起夜是常发现母亲不在炕上,半睁着迷糊的眼睛瞅了半天,才发现她正披着衣服挨个查看那些黑瓦缸。有时候,她会猛然拔掉一些缸子靠近底部的一个小圆眼上的细长木塞,于是就看见一股淡黄色的汁液从那个小圆孔里汩汩地流淌出来,跌入地上放着的一个大瓷盆里。等盆子接满后了,母亲再把它们全部倒回大瓦缸里,如此反复数十次,直到那些流出的汁液变成黑红色,喝起来酸而不涩,醇而不烈,才算是最终酿成了好醋。在我看来,醋尽管好喝,但是酿造过程却是如此的复杂和艰难,正应了老一辈人说的那句话:“好事多磨”。
我大概是小时候在母亲酿醋的时候经常喝醋,所以后来才养成了喜欢吃醋喝醋的习惯。没想到我的好吃醋,竟然也影响了身边的几个朋友。记得一个汉中的和我同姓的老同事,以前不怎么吃醋,和我在一起久了,慢慢也喜欢了吃醋。我曾经从老家带来一壶醋给他,他吃完之后还老问我要,而且声明必须是我老家的醋。还有一个五六年前的老同事,家是渭南的,他前段时间来西安看我,闲聊时说起西府的醋,说是我曾经给他送过一壶醋,她媳妇一直舍不得给锅里放,常常一个人用杯子倒一点出来慢慢喝,像品尝美酒一样。我听了之后,大为感动,很想回家给他再多拿些醋过来。但是母亲现在上了年纪,身体大不如从前,已经好几年不做醋了,我家现在吃的醋是我大姐供应的。我大姐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真传,好歹这门酿醋的工艺没有失传,我心里倒也挺欣慰。后来,听说我们镇上的建忠集团创建了一家醋厂,我还曾过去参观过一次,采用的是一套现代化先进设备和生产工艺,生产的香醋品质更高、口味醇香,远销全国各地。
据说,醋这东西和酒的酿造工艺差不多,但是它不像酒那样好储存。醋储存得好了,颜色越发黑红,有红酒一样的颜色,白酒一样的香味,吃起来香醇柔和;如果储藏不好,超不过半年就坏了,颜色变成淡黄色,甚至还会生出白花和蛆虫,味道苦涩不堪,难以入饭。
其他地方的酿醋工艺和过程,我从未亲眼目睹过,但是想必应该也差不多,但是我吃遍了天下的醋,却感觉只有我们关中西府农家醋的味道最纯、最正、最香!
陕西辣子
“江西人不怕辣,湖南人辣不怕,四川人怕不辣。”四川和湖南人爱吃辣椒是全国有名的,实际上江西人吃辣椒似乎不太被人们提说。其实,还有一个地方的人特别爱吃辣,那就是陕西人。
陕西人通常把辣椒叫作“辣子”,往往“没有辣子吃不下饭”。陕西著名作家贾平凹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:“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,三千万人民齐吼秦腔,捞一碗长面喜气洋洋,没调辣子嘟嘟囔囔。”爱吃辣子到如此地步,那就是一种嗜好了。因嗜辣如命,陕西人多数脾性甚大,其暴似火,其烈如辣。
陕西人,尤其是关中地区人素以面食为主,吃面食往往离不开辣子。但陕西人吃辣子不同其他地方人。四川、湖南、江西等地方的人爱吃炒菜、米饭,他们往往是把辣角干放在菜里去炒,当作一种佐料,实际上很少直接食用。而陕西人就不同了,他们把红红的干辣子磨成面儿,用煎油泼了之后抄在面食里吃;还有一种吃法,就是把馍切成两张薄片儿,蘸上油泼辣子,撒上一层盐巴,两张馍片扣在一起,这叫“辣子夹膜”。“油泼辣子”看着红、闻着香、吃着辣。陕西有“八大怪”,其中一怪就是“油泼辣子一道菜”。由此可见陕西人吃辣子的厉害程度,这也是陕西人的实在之处。
陕西盛产辣子,以关中地区最为集中。宝鸡、咸阳、渭南都种植辣子,但要论品质、产量和名气,那算是西府宝鸡的辣子了。前一段时间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最新消息,说是宝鸡辣子最近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品牌。宝鸡辣子在陕西乃至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见一斑。
我的家乡扶风县,隶属宝鸡市管辖,那里大面积种植辣子。辣子喜水但不喜阴,因此它最适宜在沙土地里生长。因此,地处我们扶风县最南边渭河沿岸的绛帐镇、上宋乡一带是盛产辣子的好地方。
在我们家乡,辣子从育苗、栽培、管理到采摘,历时八九个月。每年正月十五一过,天气转暖,乡亲们就开始春忙了。他们在自家门前的空场开辟一片地作为辣子苗床。育苗是第一道程序,相当麻烦:先是用䦆头把地深翻一遍,施上晒干的农家肥,把土块敲碎打匀,用刨耙刨成一个个一米宽的地垄;然后把提前培育的辣籽芽撒在地垄里,再用钉耙搂匀,在两边的堎上插上树枝条,用细布条绑紧,再在这一绺弓形枝条上横向固定一根长竹竿,最后盖上塑料纸,这就成了一个大棚辣子苗床。苗床弄好后,把水引到里面浇一下,几天后,辣子苗就破土而出,细细的嫩苗齐刷刷得很好看,颜色先是淡绿,再过几天就渐渐变成了深绿。
春夏之交,辣子苗就长到一乍多高了。这时候,人们就把它们从苗床里拔出来栽到地里去了。那时节,渭河南北两岸的田地上,到处可见家家户户在地里栽植辣子苗,一垄连一垄,一片连一片,好不壮观!辣子苗栽好,沟施了化肥,再浇上一遍水,暂时就不用管了。辣子苗吸收了充足的阳光、水气和养料,要不了一周就换样了,再过三四周变分生出好多枝丫,叶子郁郁青青,长势煞是喜人。
七月份,辣子苗秆长大了,主干虽然不粗壮,但枝叉纵横。辣子秆伸展着枝条,一片片椭圆的叶子挨挨挤挤的。辣子树上开出朴素细碎的白花,星星点点,甚是可爱。等花儿谢了以后,枝头就开始冒出嫩嫩的辣子尖儿。再经过一段时间,小辣子就长大了,头圆圆的,身子长长的,尾巴尖尖的,身上散发着油光。那段日子,你不时会看到农家妇女置身其间,或除草灭虫,或浇灌施肥,工作甚为精心细致。
辣子新长出来时是淡绿色的,慢慢变成深绿色,再慢慢变成橘黄色、酱红色,最后才会变成那种通体发亮的大红色。在新鲜辣子还是绿色的时候,乡亲们经常会摘下一些来,清洗干净,在锅里稍微煮一下,去掉其中的涩味,然后切成小段儿,放上一些其他佐料凉拌或用煎油泼过之后,就着苞谷糁子和馒头吃,味道鲜美馋人。连四五岁的小孩,也常经不住它的诱惑,尽管吃了之后会哭,但哭了之后还要再吃。
到了八月份,绿辣子便相继红起来。有的又弯又尖,身段儿不长,好像一把小镰刀,这种叫作“朝天椒”。这种辣椒虽然可爱,但是不好卖,所以乡亲们并不喜欢。大部分的鲜红辣子又长又直,密密匝匝地集结在一起,采摘时可以一把把地捋,很是方便,我们当地人称之为“线线辣子”。其实,我们家乡的辣子,品种特别繁多,好多名字我都叫不上来。
辣子一红,乡亲们就开始一批一批地采摘了。那时正是暑期,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男女老少弓着腰在辣子地里说说笑笑忙活着。每年这个时候,外地的商贩常常赶到我们这里,。有时候,收辣子的商贩太多,有些人为了能抢收到更多的好辣子,会把车直接开到人家的地头去,连里面的绿叶都不拣,直接扛出地头去过秤、装车,然后销往全国各地,家乡的辣子由此而声名远扬。
当然,也有一些乡亲为了卖上好价钱,把辣子拉到绛帐街道或火车站零售,再不好的辣子一天下来也能全部卖完。尤其是逢着赶集的日子,天刚麻麻亮,就可以看到很多农民伯伯、年轻的小伙、姑娘骑着自行车驮着大筐小筐的辣椒,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集市上去。一时间,街道上、农贸市场里几乎成了一片红辣子的世界。
除了销售之外,我们还会给自家留一些上好的鲜红辣椒。妇女们常用细线把鲜红辣子串联起来,然后挂在房前檐下晒干。晒干了的辣子就会变得干瘦、拧巴,颜色成了暗红。等平时吃用的时候,把辣子串串拆解下来,摘去蒂把,用剪刀剪成小段儿,在铁锅里用文火炒一下,最后放在僵石窝里砸成面儿,封存在瓶瓶罐罐里,供以后做油泼辣子用。其实,除了干辣面之外,辣子制品花样还有很多:腌青椒、辣椒酱、辣子油等等。
辣子虽辣,但辣得有味,辣得过瘾。因此,陕西人常禁不住那火红火红辣椒的诱惑,以至于将它视作“宝贝”了。陕西人不管是外出旅游、公差、求学还是务工,若无辣椒,则食欲不振、茶饭不思,于是就想方设法弄些辣椒来佐饭,或高价购买,或家中邮寄,或出门自带。陕西人去外地,吃不上好面条,上餐馆也都少不了点上几道带辣子的菜。这也是川菜、湘菜在陕西能得以普遍流行的原因。九十年代末期,我外出求学,吃不惯学校食堂的大锅菜。每次回家,都会带一些油泼辣子或辣子酱。每次带过来,本想独自偷偷享用,但总是要不了几天就被宿友们人瓜分完了,自己实际上吃不上几口,心里那个恨呀……
辣子虽辣,但营养丰富。辣子里的维生素C含量非常高,在蔬菜中可是首屈一指;它的氨基酸含量也非常丰富。难怪有人称它为“营养炸弹”呢!辣子不仅是大家喜欢的蔬菜、调味品,还算是一种药材呢,它有健骨、祛风、行气、散血等作用。适量地食用辣子,还可以增进食欲、促进消化。
作为一个地道的陕西人,我从小对辣子情有独钟。我吃辣子时只感觉到它的香,从来没觉得它的辣;至于其营养价值,我是从来就没考虑过。我吃辣子的量,身边的好多陕西朋友也都觉得惊讶,外地的朋友则是嗔目结舌了。我小时候在家里吃汤面,碗里的汤水常是一片血红,母亲常常会说我太浪费,我就把它们全喝下去。这些年在省城上班,常会和一些外地的朋友同桌吃饭,点菜的时候也会点带辣子的,有些不能吃辣子的人就苦不堪言了。我亲眼见过江苏、浙江、广东一带的朋友在我的怂恿之下学吃辣子,结果被辣得吐舌头、流眼泪,不停地喝水。于是,我就说:“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,‘吃不了辣子就干不成革命’,我们年轻人吃不了辣子就干不好工作,干不成事业……”他们常被弄得哭笑不得。
作者简介:刘省平,笔名醉墨书生,生于1979年,陕西扶风人。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陕西文学创作研究会理事、陕西职工作家协会会员、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。曾在《西安日报》《宝鸡日报》《咸阳日报》《昆山日报》《渭南日报》《番禺日报》《各界导报》《南国诗报》《华商报》《华夏散文》《黄河文学》《检察文学》《西部文学》《中国文学》《杨凌文苑》《榆林晚报》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50余万字。曾主编《西府散文选》《当代扶风作家散文选》,出版个人散文集《梦回乡关》,著有诗集《我是一棵冬天的树》。